
寫(xie) 這篇文章的時候,瑪利亞(ya) ·費爾南達·貝納維德斯(Maria Fernanda Benavides)還是德克薩斯州聖安東(dong) 尼奧市聖瑪麗(li) 學院(Saint Mary’s Hall)的大四學生。她將帶我們(men) 走進她的獲獎故事《無語》(無語)的幕後。
她告訴我們(men) 她是如何想到寫(xie) 這篇文章的:
在我的創意寫(xie) 作課上,在分析了蘭(lan) 斯頓·休斯的短篇小說《救贖》之後,我們(men) 被要求寫(xie) 一篇文章,描述我們(men) 生活中的矛盾是如何影響我們(men) 的。我立刻意識到我要把我第一次參加高中演講比賽的經曆寫(xie) 下來。
在她的評論中,瑪利亞(ya) 解釋了她是如何從(cong) 休斯的故事中汲取靈感的,她是如何精心設計一個(ge) 吸引讀者的開場白的,以及為(wei) 什麽(me) 將她的敘述刪減到600字“是發生在她身上最好的事情”。
然後,閱讀下麵瑪麗(li) 亞(ya) 的注釋,找出她的“作家的動作”,你可能會(hui) 在自己的寫(xie) 作中嚐試一下。她最初敘述的段落以粗體(ti) 字出現,原封不動地複製了這些段落,並附上了她對這些段落的評論。
《Speechless》作者:Maria Fernanda Benavides
“Mayfier ?Marfir嗎?比賽裁判一邊說一邊眯起眼睛,試圖找出拚寫(xie) 錯誤,盡管並沒有錯誤。
“這是我們(men) 。這是我的全名瑪麗(li) 亞(ya) ·費爾南達的昵稱。”
瑪麗(li) 亞(ya) ·費爾南達·貝納維德斯:一開始,我在文章中解釋了為(wei) 什麽(me) 我決(jue) 定加入演講項目,向觀眾(zhong) 介紹了導致我坐在第一輪比賽中的事件。但在編輯的過程中,我意識到我花了六段才看到故事的真正開端。
在和我的老師討論之後,我意識到開頭太描述性了,並沒有和我的讀者建立起足夠強的聯係,讓他們(men) 理解我的感受,以及我在文章結尾的變化。
最終,我決(jue) 定不以描述開頭,而是以我的名字的錯誤發音開始文章,以一種更有活力的方式傳(chuan) 達我來自另一個(ge) 國家的事實,而不是簡單地說“我不是美國人”。
從(cong) 法官艱難地把我叫到教室前麵的那一刻開始,我可以邀請我的觀眾(zhong) 和我一起經曆這段經曆。
她茫然地盯著我。
“我的父母很有創造力。”我撒了個(ge) 謊,她笑了。
我決(jue) 定讓這些句子獨立存在,而不是把它們(men) 寫(xie) 成一個(ge) 單獨的長段落,以視覺上描繪我每次被叫去表演時在房間裏感到的不適。通過用簡短的句子來分解這部分故事,我不僅(jin) 可以展示出這種互動是多麽(me) 不自然,而且還設定了一個(ge) 反映我感到尷尬的基調。
“O.K.馬赫菲爾,該你了!”
我決(jue) 定用這個(ge) 錯誤的發音來增加我的作品的輕鬆氣氛。添加幽默(在適當的時候)總是一個(ge) 很好的策略,使文章的語氣多樣化,使它更迷人!
我走到中心,掃視了一下房間,然後按照指示開始工作。我深吸了一口氣。
在這一部分,我想讓我的句子結構反映出我在執行之前的思考過程是多麽(me) 的有條理。在那一刻,我試圖記住我的教練給我的所有建議,所以我使用標點符號來創造與(yu) 我的思路相匹配的線性和直接的節奏。
我提醒自己,“用你的聲音。”
當我在表演前感到緊張時,告訴自己這些小提醒可以幫助我放鬆心情,活在當下。這是我走到教室前麵時經常做的一件事,雖然時間很短,但對我來說非常私人。我真的很想和這裏的觀眾(zhong) 分享那親(qin) 密的時刻。
我還想在文章的開頭介紹我的想法,揭露和利用我的聲音是我真正重視的東(dong) 西。通過建立這種神聖的聯係,我的聲音和它的意義(yi) ,我的讀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我為(wei) 什麽(me) 這麽(me) 傷(shang) 心,在文章的最後。
一開始我說話聲音很大,試圖掩蓋我想多了每一個(ge) 從(cong) 我嘴裏說出來的話的事實。隨著我表演的繼續,這種人為(wei) 的自信變得自然起來,我開始發自內(nei) 心地講述我作為(wei) 一名移民女性的經曆,我描述了我是多麽(me) 想念我的父親(qin) ,他每個(ge) 周末都要往返於(yu) 兩(liang) 地看望我和我的母親(qin) ,以及我對家庭的疏離感,以及我是多麽(me) 渴望有一個(ge) 我可以稱之為(wei) 家的地方。
在《救恩》中,在文章的開頭有一段,蘭(lan) 斯頓·休斯用了很長的句子,來描述他的姑媽告訴他,他被耶穌拯救後會(hui) 有一種興(xing) 奮的感覺,這啟發了我在這一段中也這麽(me) 做。
我想用更長的句子和更少的標點符號來表達我在表演時的興(xing) 奮之情。這是第一次,我不再有條不紊地思考,不再算計接下來要說什麽(me) ,不再擔心法官會(hui) 怎麽(me) 叫我的名字。那一刻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的表現。鬆散的句子結構讓我向讀者傳(chuan) 達了我正在經曆的那種完全自由的感覺。
這一段也建立了文章中第一個(ge) 基調的轉變,我從(cong) 一個(ge) 緊張和沒有安全感的人變成了一個(ge) 終於(yu) 有機會(hui) 毫無恐懼地表達自己的人。
我的表演結束了,我帶著新發現的樂(le) 觀情緒回到座位上,回想著表演如何消耗了我的精力。
現在回想起來,我本想用不同的方式描述這種感覺。我可能會(hui) 用一個(ge) 隱喻或典故來表達我經曆的轉變,而不是用“消耗”這個(ge) 詞。例如,我可能會(hui) 描述我的環境是如何變化的——房間是如何從(cong) 一個(ge) 陌生的、寒冷的環境變成一個(ge) 溫暖的、受歡迎的空間,最終讓我感到舒適。
我用我的聲音。最後。我在演講節目中找到了自己的家。
這一節對比了前一段的鬆散結構。我也借鑒了Hughes的這一技巧!在《救贖》中,大多數長段落的特點是不受約束,長句子後麵跟著簡短的陳述,作為(wei) 它們(men) 自己的段落。
通過使用象征結束的句號,而不是像逗號那樣表示繼續的標點符號,我想表明我相信我是如何被發現的;尋找屬於(yu) 我的地方的過程已經結束。
等待演講比賽公布決(jue) 賽選手的名字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每當有工作人員經過時,我都從(cong) 座位上跳了下來。我不關(guan) 心積累狀態點或個(ge) 人認可。我想有機會(hui) 再說話。
最後,一個(ge) 女孩手裏拿著一張紙走到演講張貼處,整個(ge) 自助餐廳的人都圍著她,不耐煩地等著看誰是決(jue) 賽選手。然後,我看到了。
最初,我更詳細地討論了等待過程。在我的第一稿中,我有兩(liang) 段很長的文字提到了我在等待結果時與(yu) 隊友的互動。我還寫(xie) 了一大段關(guan) 於(yu) 人們(men) 如何擠在一起閱讀帖子的內(nei) 容。
我決(jue) 定刪掉這些段落,不僅(jin) 是因為(wei) 它們(men) 轉移了觀眾(zhong) 對故事的注意力,還因為(wei) 它讓文章讀起來更像是描述而不是內(nei) 心獨白,而且敘事風格的突然變化與(yu) 文章的節奏不匹配。另外,我真的想強調,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再次體(ti) 驗那種自由的感覺。
我的文章的初稿大約有三頁長,但把它壓縮到600字是對它來說最好的事情。當我知道我隻有600個(ge) 字來講述我的故事時,我意識到我原本認為(wei) 對這篇文章至關(guan) 重要的描述和細節,實際上阻礙了我更好地描述我經曆的情感之旅。
我的名字。用稠密的黑色字母寫(xie) 的。
我之所以不寫(xie) 這一段,是因為(wei) 這是我第一次為(wei) 自己的名字感到驕傲,而不是擔心別人會(hui) 怎麽(me) 看它。我想為(wei) 這一刻建造一個(ge) 具體(ti) 的、物理的空間,因為(wei) 這對我來說是多麽(me) 的重要。
我暗自笑了。
這一次,當我走向演講課的期末考試時,我是一個(ge) 人走的,因為(wei) 我終於(yu) 獲得了在學校安靜的走廊上行走所需要的自信。我隻能聽到身後兩(liang) 個(ge) 女孩的腳步聲。
我想強調高跟鞋在我身後行走的聲音,因為(wei) 它們(men) 是一種隱喻,用來描述盡管我感覺自己獲得了平靜,但其他人對我身份的看法卻總是跟在我身後。
“我聽說聖瑪麗(li) 學院的大一新生參加了演講課決(jue) 賽,”其中一個(ge) 說,顯然是在說我。她打斷了我。我沒有看她的表演。是嗎?你看她的表演了嗎?她的演講是關(guan) 於(yu) 什麽(me) 的?她問另一個(ge) 。
“這是關(guan) 於(yu) 作為(wei) 一個(ge) 墨西哥移民。”
“哦,這就是她破產(chan) 的原因。”
“這是同樣的同情敘事,沒有什麽(me) 不同。”
我考慮過用敘述的方式來代替對話。然而,我發現,寫(xie) 下兩(liang) 個(ge) 女孩之間的對話,不給自己一個(ge) 說話的角色,讓我可以隱喻地說,我失去了自己的聲音。
突然之間,我在前幾輪比賽中獲得的信心消失了,我發現自己希望有更年長、更有經驗的隊友在我身邊,幫助我屏蔽女孩們(men) 的話。但是沒有人在那裏。
這段話以一個(ge) 長而鬆散的句子開始,然後與(yu) 一個(ge) 明確的陳述形成對比,因為(wei) 我意識到我的聲音不再是我自己的,而是別人對它的看法的解釋。它對文章的主題做了一個(ge) 微妙的評論,那就是演講節目給了我聲音,但也奪走了我的聲音。
我以為(wei) 是我的敘述讓我的話語有意義(yi) ,讓我有意義(yi) 。
我本想把這句話作為(wei) 下一段的一部分,但我最終決(jue) 定不去管它,因為(wei) 這是觀眾(zhong) 來到我頓悟開始的時刻:如果我的經曆定義(yi) 了我的聲音,但我的話卻立刻被貶低了,那麽(me) 我是誰?
這一節標誌著我聲音的轉變,說明我失去了純真。因此,我和聽眾(zhong) 不再透過玫瑰色的眼鏡來看待演講;相反,我們(men) 麵對的是這樣一個(ge) 殘酷的現實:作為(wei) 一個(ge) 外國人,在活動內(nei) 外意味著什麽(me) ?
但這並不重要。不了。從(cong) 那一刻起,我就知道自己會(hui) 在賽道上被認出是那個(ge) 墨西哥女孩,她的名字誰也不知道怎麽(me) 念。我甚至不需要談論我的身份就能被認出來。每個(ge) 人都會(hui) 認出我,不是因為(wei) 我的成就或我的存在,而是因為(wei) 我說話的獨特方式。我可以談論不同的話題,但感覺不會(hui) 有什麽(me) 不同。感覺我的聲音並沒有起到什麽(me) 作用。
“Mafer,感覺怎麽(me) 樣?”我的教練在賽後問我。“感覺很棒!”我說謊了。
我什麽(me) 都沒感覺到。不了。語言給了我聲音,但它也奪走了我的聲音。
在構建結尾的時候,我再次從(cong) 《救贖》中汲取靈感。在休斯的短篇小說的結尾,敘述者哭著入睡;他的阿姨認為(wei) 他情緒化是因為(wei) 上帝進入了他的生活,而實際上他哭是因為(wei) 他撒謊說看到了上帝,並且不再相信宗教了。
同樣地,在我的文章中,我寫(xie) 到我對我的教練撒謊說我找到了自己的聲音,而在現實中,我過去在表演中感受到的完整性和歸屬感已經消失,我不知道如何恢複。這個(ge) 謊言也與(yu) 我在文章開頭為(wei) 我的名字的性質編造的借口相吻合,我相信我已經找到了我的避風港,但最終,我還是像故事開頭那樣迷失了——隻是現在,找到歸屬感的希望也消失了,我真實的自我也隨之消失了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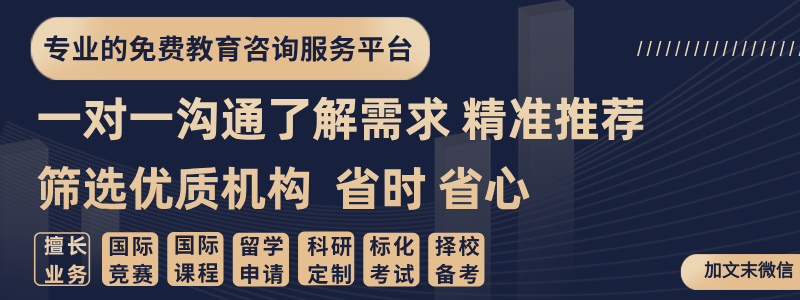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評論已經被關(guan) 閉。